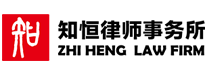企业合规对我国企业犯罪理论与实践的启示
在我国语境下,为了激励企业引入合规管理制度,有必要反思和检讨我国企业犯罪理论,尤其是企业处罚模式。当前,我国学界主要存在两种具有代表性的观点。一种是学界和司法实务者所采纳的通说,即个人抑制模式,对于企业犯罪的认定,一般只能通过企业中的“关键个人”的方式认定,而未重视企业决策机制、规章制度,以及运营模式对企业行为的影响。另一种是在我国学界产生巨大影响力的“人格化系统责任论”。该学说从法人系统的本体构造出发分析了企业犯罪的机制,是值得肯定的,但它所提出的“一个犯罪行为,两个犯罪主体”的观点,依旧没有摆脱“企业无独立犯罪能力”这一思维惯性。另外,学界提出的“新复合主体论”“单位嵌套责任论”等法人犯罪理论,本质上也是一种个人抑制模式。然而,个人抑制模式在我国单位犯罪认定中早已经受到诸多质疑,例如,(1)难以确定何人故意能够代表单位的故意;(2)“为了单位利益”“以单位名义”“违法所得归单位所有”不宜作为单位犯罪成立要件;(3)忽略单位整体背景而直接将个体意志转为单位意志的做法有时无法自圆其说;(4)在无自然人罪责可依附时单位归责存在困难。因而,在理论上完全没有必要从个人犯罪上去寻找企业犯罪的依据,而是应当分离企业责任与企业成员责任的认定路径,而非将企业犯罪作为企业组织和企业成员整体行为予以归责。
另外,在我国,刑法中的量刑规则及近几年来备受关注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主要以自然人犯罪为对象展开,还未充分考虑企业犯罪的独特性,并在此基础上对企业量刑机制予以明确化和细化。事实上,在企业犯罪的场合,除了在犯罪之后企业退赃退赔、赔偿损失、赔礼道歉以外,企业积极整改组织内部结构,采取有效的合规措施,对企业员工进行合规培训,积极协助调查,同样能体现企业的悔罪态度。为了合理限制检察官的量刑建议权以及法官的刑罚裁量权,实现量刑上的公正,有必要将企业犯罪量刑标准规范化、透明化,并明确企业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具体适用标准。
基于“越早、越严厉打击企业犯罪行为,越有利于督促企业尽早采取犯罪预防措施”的理念,我国有学者建议创建一个新的独立于传统过失犯中注意义务的刑事合规义务。毫无疑问,这个全新的刑事义务是降低企业运营中潜在风险的一个工具,但是,企业合规的刑事化同样也是一个创设刑事法律风险的过程,因此,必须十分慎重。首先,在立法操作上,设立这样一个独立的行为犯较为困难。在构成要件设置上,由于合规涉及企业运行各个环节的法律规定,合规义务的具体内容应当如何确定,什么样的合规制度可以被评价为是有效的,都难下定论。因此,这种立法可能会背离罪刑法定原则中的明确性要求。其次,刑事立法只有以法益保护为目的,自身才具有正当性。但是,在企业未制定合规体系,且未发生任何违法犯罪时,法益侵害甚至法益侵害的危险体现在哪里?退一步讲,即便确实有必要控制企业经营活动带来的法益损害风险,也应当是围绕具体领域的法益保护展开刑事立法,而不是规定一个内容宽泛的合规义务。最后,从刑事立法的手段正当即合比例原则出发,也不应在我国刑法中设立一个普遍性的合规义务。虽然独立的刑事合规义务对法益保护来说或许是适当的,但它不是实现法益保护的所有措施中对公民损害最小的那种,而且这种过于宽泛的合规义务设定与其欲实现的法益保护目的之间并不相称。我国已经建立了比较全面、完备的针对企业的行政制裁体系,因此,完全可以考虑将企业合规作为一个普遍性的行政监管激励机制。
摘自:苏州大学 蔡仙 《论企业合规的刑法激励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