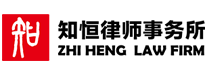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的多元化和复杂化,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之间的资金融通、商品流转的民事法律行为日益频繁,因此引发的诈骗类型的刑事案件可谓是屡见不鲜。一方面,基于民事欺诈与刑事诈骗的共同特征,刑民规范对此均有规定。在《民法典》中,“欺诈”是可撤销的民事法律行为类型,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诈骗行为集中规定在第三章“金融诈骗罪”中,其余则分散在各个章节内。另一方面,基于刑民规范的目的与主旨,合同欺诈与合同诈骗之间具有重大区分(内容、形式)。可见,涉诈骗犯罪的案件存在一种既有关联,关联中亦有融合的现象,使得此类案件成为最为复杂的一类。
我国目前司法实践中,涉诈骗类型的刑民交叉案件属疑难复杂案件。其中,对于合同诈骗罪与其合同效力的认定问题极为突出。就实践中刑民交叉案的关联形态来说,“先刑后民”、“刑民并行”虽为不少学者所主张,但在实体层面,“可能先民后刑”更具理论、立法、司法的合理性,能为合同欺诈与合同诈骗罪的界分提供一定的判断依据。
理论上,“刑民交叉案件”存在双重语境,分为刑民程序的交叉与刑民实体的交叉,前者侧重解决案件的审理模式,后者重在解决罪名认定、刑罚轻重等问题。其次,通过分析实践中刑民交叉案件的关联形态,学界可能更多关注刑民交叉案件的审理模式,而在案件的实体层面关注的少一些。基于秩序统一性立场,可以按照“先民后刑”的思路,判定实务中易被认定为合同诈骗罪的行为,分析其中的 “违法”行为究竟是合同欺诈,还是合同诈骗。最后,如果认为行为人的行为构成合同诈骗罪, 则要就“涉诈骗合同”的效力命题展开论述。
要立足于合同诈骗罪的构造对案件进行把控,根据《民法典》关于民事法律行为效力规则来分析,采用“欺诈”等手段订立的合同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无效情形,而是可撤销类型的合同,如果行为人没有隐瞒影响合同性质或目的实现的“重要事项”,即便存在欺骗方法,也不能认定为合同诈骗罪。基于刑民规范的不同价值,对涉诈骗犯罪中的合同效力的认定,应当坚持在私法范畴内。近些年的司法实践中,更倾向把诈骗行为的认定重心提前,不再刻意审查被害人是否有“财产损失”,而是重点对“诈骗”行为加以限制,判断的关键也在于行为人是否对合同中的“重要事项”进行欺骗,因此,我们在实践中也要重视限制解释与综合判断。
我国目前司法实践中,涉诈骗类型的刑民交叉案件属疑难复杂案件。其中,对于合同诈骗罪与其合同效力的认定问题极为突出。就实践中刑民交叉案的关联形态来说,“先刑后民”、“刑民并行”虽为不少学者所主张,但在实体层面,“可能先民后刑”更具理论、立法、司法的合理性,能为合同欺诈与合同诈骗罪的界分提供一定的判断依据。
理论上,“刑民交叉案件”存在双重语境,分为刑民程序的交叉与刑民实体的交叉,前者侧重解决案件的审理模式,后者重在解决罪名认定、刑罚轻重等问题。其次,通过分析实践中刑民交叉案件的关联形态,学界可能更多关注刑民交叉案件的审理模式,而在案件的实体层面关注的少一些。基于秩序统一性立场,可以按照“先民后刑”的思路,判定实务中易被认定为合同诈骗罪的行为,分析其中的 “违法”行为究竟是合同欺诈,还是合同诈骗。最后,如果认为行为人的行为构成合同诈骗罪, 则要就“涉诈骗合同”的效力命题展开论述。
要立足于合同诈骗罪的构造对案件进行把控,根据《民法典》关于民事法律行为效力规则来分析,采用“欺诈”等手段订立的合同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无效情形,而是可撤销类型的合同,如果行为人没有隐瞒影响合同性质或目的实现的“重要事项”,即便存在欺骗方法,也不能认定为合同诈骗罪。基于刑民规范的不同价值,对涉诈骗犯罪中的合同效力的认定,应当坚持在私法范畴内。近些年的司法实践中,更倾向把诈骗行为的认定重心提前,不再刻意审查被害人是否有“财产损失”,而是重点对“诈骗”行为加以限制,判断的关键也在于行为人是否对合同中的“重要事项”进行欺骗,因此,我们在实践中也要重视限制解释与综合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