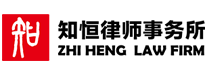刑事合规之所以在晚近二十余年呈现出强劲的全球化趋势,最直接的现实动因,在于满足国家破解治理企业犯罪所面临的系列重大难题的需要。
其一,采用传统的自然人犯罪追责方式来预防法人犯罪,其效果无异于缘木求鱼。虽然法人犯罪的能量与破坏力远胜于自然人犯罪,并且法人犯罪的机理较之自然人犯罪也全然迥异,但传统刑法中却并无专门针对法人刑事责任的规定,也即法人刑事责任是完全依附于自然人刑事责任而存在的。这对于达成预防企业犯罪的目标而言,是策略方向与路径选择上的重大错误。因为,自然人与其从属于其中的法人组织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无论个人的行为有多么重要,都只是组织价值观与活动原则的产物。组织不仅有独立于个人意志的发展愿景、奋斗目标,而且还有体现发展愿景的组织文化、制度设置与管理构架,并因此规定着、影响着身处其中的成员的守法观念与行为方式。这决定了,在自然人刑事责任模式下,即使因法人犯罪对法人组织的负责人予以处罚,并对法人追加罚金,但影响法人组织犯罪的内生性因素依然存在,故而对企业中的责任人员予以再严厉的事后惩罚,也无助于企业犯罪的减少。不仅如此,将法人刑事责任放置于个人责任基础之上,还会产生出人意料的刺激法人犯罪的恶劣后果:被定罪的法人组织依然可以我行我素,继续为了利益最大化而无视甚至蔑视法律的规训,并且不用担心组织体刑事责任风险问题。因为,一旦发生法律风险,可以轻易地通过牺牲直接涉案的中低层级的员工而转移犯罪风险;即使涉及法人组织决策人员犯罪,这也仅是其个人的责任而不是法人组织的责任。这样,虽然法律规制上名为“法人犯罪”,但真正承受惩罚的却是法人组织中的相关自然人,丝毫不能实现促使法人组织采取切实措施进行自我整改,努力消除、抑制内因性犯罪因素的组织改善功能,其结果只能是要么造成企业犯罪的恶性循环,要么打垮企业永绝后患。可以说,刑事合规制度的产生,很大程度上正是为了矫正传统法人犯罪规制中“惩罚自然人、放过法人组织”的观念与策略性错误。由此,有关企业合规就是“放过企业、严惩责任人”的理解,当属对刑事合规政策导向的误解。既给予涉罪企业“痛改前非”的机会,促使其构建能满足强化守法自我监管、有效预防犯罪的内控机制,又能克服现行专注事后惩罚容易将企业一棍子打死的制度性弊端,同时在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下惩治责任人,才是国家层面创制和推行刑事合规制度的基本政策导向。
其二,仅靠国家力量监督企业犯罪愈发力不从心,亟待制度化地引入企业力量,形成国家—企业合作预防新型治理格局。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背景下,随着企业数量的增加、规模的扩大以及经营范围与地域的扩张,单纯依靠国家力量从外部监督企业犯罪不仅效率低下,而且必然捉襟见肘。较之国家的外部监督,企业作为精细化管理的经济组织,在预防和发现内部犯罪方面有着明显优于国家的管理资源(信息资源、人力资源以及资金和技术优势等),这使得企业成为事实上的企业犯罪的最佳预防者。但作为“最佳预防者”的企业,长期以来真正关注的只是当下利润的实现,其自我预防犯罪的意愿始终处于“休眠状态”。原因何在?就在于国家层面对企业守法自我监管缺乏有效的牵引与激励机制,无法使企业将预防犯罪与维系自身生存发展联系起来。由此,就需要创设一种新型刑事制度——企业如果不顺应主动预防、发现内部犯罪的刑法规劝,将会付出难以承受的代价——以此最大限度激发企业自我预防犯罪的意愿与行动力。于是,借助已有的企业合规机制,再加入企业守法自我监管的刑事激励措施,使作为潜在的“最佳预防者”的企业能制度化地参与犯罪治理,最大限度地增强与法人犯罪作斗争的社会力量,就进入了各国刑事政策的视野。
其三,伴随着资本力量的越发强大,企业犯罪的社会危害越发深重,迫切需要开发出强有力的预防制度,以遏制资本力量的肆意掠夺与广泛渗透,确保经济平稳发展与社会的公平正义。在当代社会,企业很大程度上已成为不容忽视的政府之外的一大权力中心。大型企业,不仅在所在行业、领域享有很大的话语权和影响力,而且它们为谋求自身的发展和优势,往往有着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实现人类福祉并不完全契合的价值文化与发展战略。同时,大企业掌握着强大的物质基础,开发着影响人类未来的新产品、新技术,特别是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为大企业进行全球信息的收集、传播与操作利用提供了无限可能。在这种背景下,如果对法人犯罪依然采取等到犯罪发生后再来追责和惩罚的传统治理模式,法人犯罪将成为国家和社会难以承受之痛。
应当强调的是,国家创设刑事合规制度,不是在单向地科以企业预防犯罪的社会责任。企业构建预防犯罪的内控机制,既是基于自身社会责任的履行,也是基于企业和企业家自我发展与自我实现的需要。企业发展的历史经验已经反复告诉我们,专注于提高运营效率所获得的竞争优势只能是短暂的,唯有植根于“法规忠诚”的企业文化与运行机制,才能提升企业的内生性竞争力,并确保企业可持续的经济优势。
摘自张远煌《企业合规全球考察》
其一,采用传统的自然人犯罪追责方式来预防法人犯罪,其效果无异于缘木求鱼。虽然法人犯罪的能量与破坏力远胜于自然人犯罪,并且法人犯罪的机理较之自然人犯罪也全然迥异,但传统刑法中却并无专门针对法人刑事责任的规定,也即法人刑事责任是完全依附于自然人刑事责任而存在的。这对于达成预防企业犯罪的目标而言,是策略方向与路径选择上的重大错误。因为,自然人与其从属于其中的法人组织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无论个人的行为有多么重要,都只是组织价值观与活动原则的产物。组织不仅有独立于个人意志的发展愿景、奋斗目标,而且还有体现发展愿景的组织文化、制度设置与管理构架,并因此规定着、影响着身处其中的成员的守法观念与行为方式。这决定了,在自然人刑事责任模式下,即使因法人犯罪对法人组织的负责人予以处罚,并对法人追加罚金,但影响法人组织犯罪的内生性因素依然存在,故而对企业中的责任人员予以再严厉的事后惩罚,也无助于企业犯罪的减少。不仅如此,将法人刑事责任放置于个人责任基础之上,还会产生出人意料的刺激法人犯罪的恶劣后果:被定罪的法人组织依然可以我行我素,继续为了利益最大化而无视甚至蔑视法律的规训,并且不用担心组织体刑事责任风险问题。因为,一旦发生法律风险,可以轻易地通过牺牲直接涉案的中低层级的员工而转移犯罪风险;即使涉及法人组织决策人员犯罪,这也仅是其个人的责任而不是法人组织的责任。这样,虽然法律规制上名为“法人犯罪”,但真正承受惩罚的却是法人组织中的相关自然人,丝毫不能实现促使法人组织采取切实措施进行自我整改,努力消除、抑制内因性犯罪因素的组织改善功能,其结果只能是要么造成企业犯罪的恶性循环,要么打垮企业永绝后患。可以说,刑事合规制度的产生,很大程度上正是为了矫正传统法人犯罪规制中“惩罚自然人、放过法人组织”的观念与策略性错误。由此,有关企业合规就是“放过企业、严惩责任人”的理解,当属对刑事合规政策导向的误解。既给予涉罪企业“痛改前非”的机会,促使其构建能满足强化守法自我监管、有效预防犯罪的内控机制,又能克服现行专注事后惩罚容易将企业一棍子打死的制度性弊端,同时在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下惩治责任人,才是国家层面创制和推行刑事合规制度的基本政策导向。
其二,仅靠国家力量监督企业犯罪愈发力不从心,亟待制度化地引入企业力量,形成国家—企业合作预防新型治理格局。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背景下,随着企业数量的增加、规模的扩大以及经营范围与地域的扩张,单纯依靠国家力量从外部监督企业犯罪不仅效率低下,而且必然捉襟见肘。较之国家的外部监督,企业作为精细化管理的经济组织,在预防和发现内部犯罪方面有着明显优于国家的管理资源(信息资源、人力资源以及资金和技术优势等),这使得企业成为事实上的企业犯罪的最佳预防者。但作为“最佳预防者”的企业,长期以来真正关注的只是当下利润的实现,其自我预防犯罪的意愿始终处于“休眠状态”。原因何在?就在于国家层面对企业守法自我监管缺乏有效的牵引与激励机制,无法使企业将预防犯罪与维系自身生存发展联系起来。由此,就需要创设一种新型刑事制度——企业如果不顺应主动预防、发现内部犯罪的刑法规劝,将会付出难以承受的代价——以此最大限度激发企业自我预防犯罪的意愿与行动力。于是,借助已有的企业合规机制,再加入企业守法自我监管的刑事激励措施,使作为潜在的“最佳预防者”的企业能制度化地参与犯罪治理,最大限度地增强与法人犯罪作斗争的社会力量,就进入了各国刑事政策的视野。
其三,伴随着资本力量的越发强大,企业犯罪的社会危害越发深重,迫切需要开发出强有力的预防制度,以遏制资本力量的肆意掠夺与广泛渗透,确保经济平稳发展与社会的公平正义。在当代社会,企业很大程度上已成为不容忽视的政府之外的一大权力中心。大型企业,不仅在所在行业、领域享有很大的话语权和影响力,而且它们为谋求自身的发展和优势,往往有着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实现人类福祉并不完全契合的价值文化与发展战略。同时,大企业掌握着强大的物质基础,开发着影响人类未来的新产品、新技术,特别是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为大企业进行全球信息的收集、传播与操作利用提供了无限可能。在这种背景下,如果对法人犯罪依然采取等到犯罪发生后再来追责和惩罚的传统治理模式,法人犯罪将成为国家和社会难以承受之痛。
应当强调的是,国家创设刑事合规制度,不是在单向地科以企业预防犯罪的社会责任。企业构建预防犯罪的内控机制,既是基于自身社会责任的履行,也是基于企业和企业家自我发展与自我实现的需要。企业发展的历史经验已经反复告诉我们,专注于提高运营效率所获得的竞争优势只能是短暂的,唯有植根于“法规忠诚”的企业文化与运行机制,才能提升企业的内生性竞争力,并确保企业可持续的经济优势。
摘自张远煌《企业合规全球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