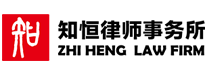“疑罪从无”的“疑”一般是指在刑事诉讼中,司法机关对受理的刑事案件经审查,在定罪与否的问题上存在疑问且未得到合理排除的一种状态。一般地讲,就是对刑事案件犯罪事实不能完全确证又无法完全排除合理怀疑,存在一种认定上的不确定性。
本期内容是《无罪辩护》的第一个案件—马廷新故意杀人案,即5·30案件。2002年5月30日,鹤壁浚县梨阳镇东马庄村一家三口被杀,在省公安厅的指示下,成立专案组,在东马庄村驻扎了100多天,同年8月30日,马廷新被抓,而案卷中记录于2002年12月14日被刑事拘留。后于同年12月25日,马廷新被批准逮捕。马廷新案件从被批准逮捕到无罪释放,历经了五年零八个月,该案件也经历了公安侦查、移送检察院审查起诉、提起公诉、一审、检察院抗诉进入二审、发回重审、检察院再次抗诉进入第二次二审,最后以“准许撤回抗诉,驳回上诉人的上诉,维持刑附民的附带民事部分(马廷新无罪,不承担民事赔偿责任)”落下帷幕。漫漫长路,经过作者深入研究案卷以及大量的调查研究后提出的多处疑点、马廷新及其家人的耐心等待,迟到的正义究竟还是来了。上述案件时间跨度长,不但在于该案疑难复杂,也在于当时的侦查手段存在不公,使得定罪证据存在多处疑点,难以排除合理怀疑。
马廷新故意杀人案是作者无罪辩护的首起要案,其在讲述此案件过程中,提及了“测谎”证据、刑讯逼供、疑罪从无等要素,这些要素是本案件中的主要突破口,笔者结合书中内容以及网上检索,先来讲讲“测谎”。
CPS(Computerized Polygraph System)多道心理测试,俗称测谎,这种技术来源于俄罗斯和美国,我国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引进和研究测谎技术,并首先在刑事侦查中运用。关于“测谎结论”的法律属性,主要有三个说法:一是侦讯类,二是勘验类,三是鉴定类。1999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在《关于CPS多道心理测试鉴定结论能否作为诉讼证据使用问题的批复》中指出:“人民检察院办理案件,可以使用CPS多道心理测试鉴定结论帮助审查、判断证据,但不能将CPS多道心理测试鉴定结论作为证据使用。”由此可得出,且从证据能力和证明力的角度上看,“测谎结论”不是证据,目前在我国不能作为证据使用,所以不能作为法官审判案件的参考和依据。但随着科技的进步、社会的发展,“测谎结论”究竟能否作为证据使用,仍有待考究。
在马廷新案件中,马廷新就是因为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仅靠“测谎结论”就被确定为“凶手”,并被立即采取了强制措施。在当时,也不乏因为“测谎结论”被认定为犯罪嫌疑人,而最后因证据不足撤案的例子;因“测谎”错误而引发冤案也大量存在。就如书中谈及的“钟祥四教师投毒案”,钟祥一学校师生在食堂吃完早餐后不适,好在送往医院抢救后脱险,经调查,发现食物中有剧毒药物成分。该案在侦查期间,警方通过“测谎”认定了四名教师为犯罪嫌疑人,并在随后的审讯中,该四名教师承认了投毒事实。但在案件移送法院进行审理时,四名教师全部翻供,并称受到了刑讯逼供。最后,该案因证据不足,警方决定撤销。
根据以上内容,作者得出了一个结论,这结论相信你也不难发现,就是:一旦测谎将嫌疑人锁定于某个无辜者,那么,在没有其他证据的情况下,侦查人员极其有可能更加确信所冤枉的无辜者就是凶手,为了获取口供以及更多的证据或者线索,逼供自然不可避免。基于当时背景,结合当时案件情况,得出如此结论也是有理有据。但笔者相信,在如今的法治社会,程序正义不断彰显,刑讯逼供等违法手段已鲜有出现,一旦出现并查实也绝对不得容忍,因为这不仅是对人权的侵犯,更是对法律权威的挑战。
本期内容就到这里,下期笔者继续《无罪辩护》第一案的内容,说说马廷新案中提及的刑讯逼供以及疑罪从无。
本期内容是《无罪辩护》的第一个案件—马廷新故意杀人案,即5·30案件。2002年5月30日,鹤壁浚县梨阳镇东马庄村一家三口被杀,在省公安厅的指示下,成立专案组,在东马庄村驻扎了100多天,同年8月30日,马廷新被抓,而案卷中记录于2002年12月14日被刑事拘留。后于同年12月25日,马廷新被批准逮捕。马廷新案件从被批准逮捕到无罪释放,历经了五年零八个月,该案件也经历了公安侦查、移送检察院审查起诉、提起公诉、一审、检察院抗诉进入二审、发回重审、检察院再次抗诉进入第二次二审,最后以“准许撤回抗诉,驳回上诉人的上诉,维持刑附民的附带民事部分(马廷新无罪,不承担民事赔偿责任)”落下帷幕。漫漫长路,经过作者深入研究案卷以及大量的调查研究后提出的多处疑点、马廷新及其家人的耐心等待,迟到的正义究竟还是来了。上述案件时间跨度长,不但在于该案疑难复杂,也在于当时的侦查手段存在不公,使得定罪证据存在多处疑点,难以排除合理怀疑。
马廷新故意杀人案是作者无罪辩护的首起要案,其在讲述此案件过程中,提及了“测谎”证据、刑讯逼供、疑罪从无等要素,这些要素是本案件中的主要突破口,笔者结合书中内容以及网上检索,先来讲讲“测谎”。
CPS(Computerized Polygraph System)多道心理测试,俗称测谎,这种技术来源于俄罗斯和美国,我国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引进和研究测谎技术,并首先在刑事侦查中运用。关于“测谎结论”的法律属性,主要有三个说法:一是侦讯类,二是勘验类,三是鉴定类。1999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在《关于CPS多道心理测试鉴定结论能否作为诉讼证据使用问题的批复》中指出:“人民检察院办理案件,可以使用CPS多道心理测试鉴定结论帮助审查、判断证据,但不能将CPS多道心理测试鉴定结论作为证据使用。”由此可得出,且从证据能力和证明力的角度上看,“测谎结论”不是证据,目前在我国不能作为证据使用,所以不能作为法官审判案件的参考和依据。但随着科技的进步、社会的发展,“测谎结论”究竟能否作为证据使用,仍有待考究。
在马廷新案件中,马廷新就是因为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仅靠“测谎结论”就被确定为“凶手”,并被立即采取了强制措施。在当时,也不乏因为“测谎结论”被认定为犯罪嫌疑人,而最后因证据不足撤案的例子;因“测谎”错误而引发冤案也大量存在。就如书中谈及的“钟祥四教师投毒案”,钟祥一学校师生在食堂吃完早餐后不适,好在送往医院抢救后脱险,经调查,发现食物中有剧毒药物成分。该案在侦查期间,警方通过“测谎”认定了四名教师为犯罪嫌疑人,并在随后的审讯中,该四名教师承认了投毒事实。但在案件移送法院进行审理时,四名教师全部翻供,并称受到了刑讯逼供。最后,该案因证据不足,警方决定撤销。
根据以上内容,作者得出了一个结论,这结论相信你也不难发现,就是:一旦测谎将嫌疑人锁定于某个无辜者,那么,在没有其他证据的情况下,侦查人员极其有可能更加确信所冤枉的无辜者就是凶手,为了获取口供以及更多的证据或者线索,逼供自然不可避免。基于当时背景,结合当时案件情况,得出如此结论也是有理有据。但笔者相信,在如今的法治社会,程序正义不断彰显,刑讯逼供等违法手段已鲜有出现,一旦出现并查实也绝对不得容忍,因为这不仅是对人权的侵犯,更是对法律权威的挑战。
本期内容就到这里,下期笔者继续《无罪辩护》第一案的内容,说说马廷新案中提及的刑讯逼供以及疑罪从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