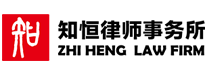刑法第287条之二第一款规定: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为其提供互联网接入、服务器托管、网络存储、通讯技术传输等技术支持,或者提供广告推广、支付结算等帮助,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单处罚金。帮信罪是帮助行为的正犯化,是独立的罪名,构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有其明确的罪状规定,符合罪状规定的就是本罪的实行行为。对“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的“犯罪”范围的讨论,最核心的就在于是否承认没有达到法定罪量要素的信息网络违法行为属于帮信罪的对象。
在司法上正犯化拥有三种模式:
第一种模式 ,提供帮助的行为成立被帮助犯罪的共同犯罪,被帮助的犯罪行为必须达到法定的罪量要素;
第二种模式,提供帮助的行为成立被帮助犯罪的共同犯罪,被帮助的行为不是必须达到自身构成犯罪所要求的法定罪量;第三种模式:直接将共犯行为视为独立的实行行为且不要求正犯达到其本身的法定罪;
第三种模式与第二种模式的根本区别在于,定性不再明确共犯行为必须要与正犯行为构成“共同犯罪”,而是直接规定共犯行为的定罪量刑标准,达标即直接适用刑法的相应条款。对于帮信罪,应采取第三种模式。
帮信罪作为一个具备“实质帮助犯性质”,但是已经被正犯化了的独立罪名,与其他分论各罪一样具有该罪的保护法益,对“犯罪”一词的界定需要结合帮信罪的保护法益来确定。
帮信罪是不同主体作为或不作为的违规的非法使用网络技术,妨害网络空间公共秩序的行为,对于其所帮助的信息网络犯罪若严格按照共犯从属性的解释思路,只有依照分则各罪的规定,在四要件下具备主体、主观方面、客观方面、客体,在三阶层下具备构成要件该当、违法与有责,成立犯罪的情况下,帮信罪才成立,无疑是严重的缩小了帮信罪的成立范围。这是极端从属性说的解释思路带来的问题,也是在设立帮信罪之前就面临的问题。而采取限制从属性说,个别判断责任,在正犯未达刑事责任年龄或者具有其他责任阻却事由的情况下,仍然追究共犯的责任。在这种解释思路下,虽然解决了一部分问题,但是未达罪量要求的情形,仍然不能纳入帮信罪“犯罪”的范围。
实务当中面对的制裁难题便是网络帮助“一对多”的情形。在帮助单个未达罪量要求的信息网络犯罪时,按照限制从属性的解释思路不构成帮信罪,再从法益侵害性的角度考量也无可厚非。但是在帮助海量的未达罪量要求的信息网络犯罪时,如果还按照限制从属性的解释思路,认为不构成犯罪,从法益侵害角度考量,就得不出合理结论了。这是帮信罪“积量构罪”的特征,也是其独立性的表现。帮信罪处在共犯性和独立性的纠缠之中,正如上文所言,其无法完全摆脱共犯性的限制,但是却可以克服共犯性的藩篱,在这种纠缠中,让共犯性退步至一个合理的程度,而为独立性创造更大的发展空间。
在“犯罪”界定问题上,最小从属性说或许更能在最大限度上满足帮信罪独立性的要求, 合理的划定被帮助行为的范围,解决制裁困境。帮信罪之“一对多”(未达罪量要求)是典型的“无正犯的共犯”的情形。按照最小从属性说,成立共犯,只要正犯行为能够被评价为实行行为即可;并且,处罚共犯的理由不在于其参与了其他人的“违法的”实行行为,而在于其“违法地”参与了他人的实行行为。未达罪量要素的分则类型化的犯罪行为可以被评价为犯罪实行行为,帮信罪的主体正是帮助了海量的类似行为而具有了积量的社会危害性。
从体系性的角度考察,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是将信息网络违法、犯罪的预备行为予以正犯化,而提前处罚的行为,其使用的“违法犯罪活动”的表述,有更大的解释空间。限于罪刑法定原则,对帮信罪“犯罪”的解释不能超过法条文用语的极限,从而不能包含违法行为在内,但是预备行为相较于帮助行为是法益侵害的紧迫性更缓和的行为,却包含了违法行为和犯罪行为,对于帮助行为若采取较为严格的解释并不合理,也与立法的目的不相符合。
从文义解释的角度考察,“犯罪”一词具有多义性,并不一定要解释为完全符合构成要件的犯罪,将其解释为没有达到罪量标准的犯罪类型行为(如刑法第269条转化型抢劫的前提罪名),从行为性质上来理解“犯罪”一词的含义并没有违背一般国民的预测可能性
综上,对于帮信罪“犯罪”的界定,应采取一种宽松的解释态度,用最小从属性来协调帮信罪正犯性和共犯性之纠缠,将“犯罪”的范围扩张到符合分则客观构成要件特征,未达罪量标准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