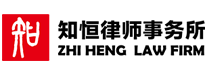在企业合规改革中, 理论和实务界中存在的一个误区就是大规模企业在刑事合规整改中有能力也有必要建立一套专项性甚至整体性的合规体系, 而中小微企业没有能力也没有必要建立一套专项性的合规体系, 采取纠错性合规的方式就足够了。 这种观点反映了对制度确定性的追求, 希望合规整改的过程中有一个较为确定的标准。 但是,如果仅仅将企业合规整改方式选择的影响因素限于企业规模,就很容易导致将本可能适用专项合规的中小微企业或本可能适用纠错合规的大型企业放在确定性合规选择方式话语所构筑的普洛克鲁斯蒂之床。 因此,企业刑事合规整改方式的选择也如同制度的建构一样不是简单地依据企业规模的大小就能决定的, 企业刑事合规整改恰当标准的设置, 即选择专项性合规还是纠错性合规, 应当充分考虑企业合规效果的影响因素, 再对各项影响因素进行综合分析, 选择使企业合规整改效用最大化的方式。 当然, 在实践中所有影响因素不可能面面俱到, 影响因素的选择也需要兼顾司法效率。 最为恰当的方法就是选取几项对企业合规整改效果影响最大的因素进行考察。一般来讲, 企业刑事合规整改中合规整改期限、 企业涉罪类型、 企业规模、 企业文化、 企业对检察机关合规激励的预期对企业合规整改方式的选择以及企业合规整改效果的影响最大。 其中, 企业刑事合规整改期限与企业规模是相对客观的评价标准, 企业涉罪类型是既主观又客观的评价标准, 而企业文化以及企业对检察机关合规激励的预期是相对主观
的评价标准。
第一, 合规整改期限对企业刑事合规整改方式的选择具有较大的影响, 企业合规整改的期限越长, 企业更适合建立一套专项性的合规体系, 而企业合规整改期限越短, 企业针对专门的刑事风险领域建立一套纠错性合规体系可能更为合适。 就目前的情况而言, 由于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只及于未成年人, 企业合规整改不能使用附条件不起诉的制度。因此, 企业刑事合规整改成功后的最终结果一般都是对企业作出相对不起诉的处理。 在相对不起诉的框架下, 理想状态下企业合规整改的期限最长是一年, 而通过分析企业合规指导案例可知,在实践中企业合规整改的期限设置一般没有超过六个月, 比如在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指导性案例中, 张家港市检察机关对张家港市 L 公司设置了两个月的合规考察期限, 上海市检察机关对上海市 A、B公司设置了五个月的合规考察期限。 虽然在现有框架下的企业合规整改的期限普遍较短, 无论什么样的企业在几个月的时间里建立一套专项性合规体系难度都比较大, 但是 6 个月的时间和 3 个月的时间仍然存在差别, 企业合规整改的期限设置越长, 企业建立一套专项性的合规体系的可能性就越大, 就可以有倾向性地匹配基础性合规条件下的专项性合规整改计划, 而企业合规整改期限设置越短就越应该匹配纠错性合规整改计划。 如果在合规整改期限较短的情况下, 企业还匹配基础性合规条件下的纠错性合规整改的话, 企业就可能为了迎合合规审查小组最终的合规审查标准而进行形式上的合规整改, 而不是针对本企业实际需求进行合规整改, 最终可能出现以牺牲企业需要换取程序上的轻缓处理的问题。 总之, 对涉案企业合规计划实施考察期进行区别规定, 是对不同规模企业的灵活考虑和科学设计, 有利于企业根据法律要求进行企业合规建设和管理。值得注意的是, 企业合规整改期限的设置通常是依据企业选择的合规方式决定的, 但是企业和第三方组织对可能的合规审查期限的预期反过来也会影响企业对合规审查方式的选择, 企业合规整改期限与企业合规整改方式是互相匹配的关系。
第二, 企业涉罪类型也与企业合规整改方式具有对应关系。 有学者将涉企犯罪的类型区分为系统性犯罪与非系统性犯罪, 系统性犯罪是经过企业集体性决策或者由企业管理层决定所实施的犯罪, 非系统性犯罪是由其他某一个体以企业的名义并为企业的利益而实施的犯罪。 12& 该分类方式对于企业合规整改的选择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现在学界较为主流的观点认为, 合规出罪制度只能及于较轻的犯罪, “程序出罪” 不能明显背离 “罪责刑相一致”的刑事归责框架, 而企业犯罪中罪行轻重的界定通常涉及到企业犯罪的危害结果和 “组织体的再犯危险性” 两个方面。因此, 企业合规整改方式的选择通常与企业涉罪严重程度相关。 如果企业所涉罪类型属于系统性单位犯罪 (说明企业的 “组织体的再犯危险性” 较大) 且造成的危害结果较大,其社会危害性较大, 整改难度也更大, 企业要想在 “罪责相一致的” 原则下获得从轻减轻处罚的量刑建议甚至 “程序出罪” 的处理, 那么企业就必须要进行基础性合规条件下的专项合规整改, 包括重新制定公司章程安排公司经营管理模式、 重组董事会、 改组管理层、 将责任人员移交检察机关、 大规模的公司内部培训等。 如果企业所涉罪类型属于非系统性的单位犯罪且危害结果较小, 其整改相对来说较为容易, 且这种类型的企业犯罪的原因多为经营管理中某一环节或者说某个部门、 某个个人出现了问题, 那么企业就可以针对具体的涉罪风险和企业经营管理特定环节进行纠错性合规整改。 在实践中还有一种情况是企业自身没有构成犯罪, 但是由于企业的相关管理制度和实践的疏漏导致企业成为个人犯罪的受害者, 企业可以自愿进行刑事合规整改。那么这个时候就可以根据个人犯罪的严重程度和企
业合规制度漏洞的大小及危险系数选择企业合规整改的方式。 总的来说, 根据企业不同的涉罪情况选择不同程度的整改方式不仅可以使企业合规整改实现罪责相适应, 与企业涉罪情况相匹配的合规整改方式还能使合规整改在资源配置最优的情况下达到祛除企业犯罪 “基因” 的目的。
第三, 企业的规模对合规整改方式的选择以及合规整改的效果的影响一般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 一般大型企业的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更为雄厚, 而小型企业的相关资本就要欠缺一些。 企业合规整改中首先需要大量资金的投入, 主要包括由企业支付的第三方组织的费用和建设企业合规体系的专项资金, 专项合规需要的合规第三方人员数量和水平自然高于仅进行一两项纠错合规, 并且建设基础合规条件下的专项性企业合规体系的专项资金需求更多。 因此, 专项性合规所要投入的合规资金要比只进行一两项纠错性合规的资金多得多, 在企业合规整改的过程中, 大型企业更有能力选择专项性合规的方式, 而中小微企业更适宜采取纠错性合规的方式。 同时, 企业合规整改还需要大量人力资本的投入, 中小微企业限于企业规模, 其人力资本可能具有局部专门性的特征。 如果要在中小微企业建设一套整体性合规体系, 那么中小微企业势必要补充相关的人力资本, 这对于中小微企业来说也是一项不小的成本。 考虑到人力资本的限制, 中小微企业采取纠错性合规方式更为适宜。 另一方面,大型的涉罪企业可能本身就具备许多基础性的合规制度, 比如已经建设了相应的合规组织、 初步的合规审查机制与末端业务合规评估机制、 一定的合规程序, 在此基础上建立专项性合规制度就更为容易,其所花费的物力、 人力与时间成本甚至比中小微企业进行一两项纠错性合规的成本还要低。 基于经济条件和现实成本的考量, 大型企业在已有基础性合规架构情况下建设专项性的合规体系可能是更优选择, 而中小微企业在缺乏基础性合规架构的情况下进行纠错性的合规建设可能更为合适。 比如就企业税务合规整改而言, 中小微企业税务风险产生的原
因可能在于内部合规管理团队缺乏、 企业税务合规管理制度不健全、 企业业绩评估机制忽视纳税问题、 企业领导层税务风险意识缺乏等。涉及税务合规问题的中小微企业限于基础性合规制度的缺乏, 可能难以在零基础的情况下对整个企业的合规团队和合规管理制度进行建设, 在这种情况下涉罪中小微企业采取针对税务部门的纠错性合规整改更为合适, 如将企业的纳税问题纳入公司的业绩评估以及公司管理层集体学习税务合规方面的知识等。当然, 在实际合规整改方式的选择中不能完全依照企业规模进行 “一刀切” 的判断, 有些中小微企业可能也具备良好的基础性合规管理体系, 并且有条件选择专项性合规的方式, 那么对于这种企业可以结合企业的人力、 物力资本情况对合规整改方式的选择进行综合判断。
第四, 企业文化在合规整改方式的选择上也会产生较大的影响。 现有企业合规改革中, 关于企业文化的研究主要在于企业文化与企业责任的关系。有学者认为, 企业文化比企业合规体系的建设情况更为适合作为企业是否进行刑事归责, 企业合规体系只是企业文化的一个表象, 并且企业合规计划越完整, 违法行为就越有可能暴露给政府人员和潜在的竞争对手, 增加企业被追究刑事责任或民事责任的风险, 有可能导致企业的 “纸面” 合规体系。 有国外学者认为, 应当在 《联邦量刑指南》 中用企业文化责任论取代企业合规计划。 但也有学者认为企业文化不能作为企业刑事规则的标准, 因为公司文化仅仅是公司治理的附随产品, 并且企业文化的判断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 17# 在实践中, 企业文化作为一种主观性判断较多的因素, 确实不宜直接用于企业刑事责任的归责或者企业合规整改是否有效的标准。 但是在企业合规整改方式的选择中,企业文化可以作为一种企业合规整改方式选择的判断因素。 例如, “家文化” 有其独特的、 强烈的穿透力, “家文化” 在各种社会组织中的可接受性都较强。一些小微企业甚至规模较大的民营企业的企业文化通常是以 “企业家才能” 为主导的 “家文化”。在企业管理实践中, 通过制度化、 规范化维持的契约关系与通过人与人之间的情感而维系的契约关系是存在张力的。 这个时候如果视这种特殊的企业文化于不顾, 在合规整改的过程中机械性地选择基础合规条件下的专项性合规方式, 可能会对关涉到企业经营发展根基的企业文化产生不利影响, 甚至导致企业无法在新的合规管理体系中正常运行, 与企业合规改革中 “拯救一个企业” 的理念相悖。 因此, 企业和第三方组织在确定企业合规整改方式的
时候需要关照企业的文化类型, 如果企业经营管理模式倾向于 “通过人与人之间的情感而维系的契约关系” 模式, 那么企业在维持原有企业文化不变的情况下可以针对企业的具体风险点采取纠错性合规的方式。 而对于企业的经营管理模式本来就倾向于“通过制度化规范化维持的契约关系” 的模式, 那么企业采取专项性的合规方式与企业文化也更有契合度, 合规整改的效果可能更好。
第五, 企业对检察机关合规激励方式的预期对于企业合规整改方式的选择也有直接影响, 即检察机关对企业合规整改最终处理结果的话语能够影响涉罪企业合规整改方式的选择。 话语的分类看起来平淡无奇, 但一旦有了这些分类作为基础, 就容易理解话语的竞争和差异带来的后果。检察机关的不同话语分类能够对涉罪企业合规整改方式的选择产生不同的影响。 一般而言, 检察机关的激励话语依据程度分类可以分为以下三类: 第一类是激励程度最强的话语, 比如 “如果整改效果良好, 可能作出相对不起诉的处理”。 在这种情况下检察机关展示了较为确定且结果最好的处理话语; 此种话语下涉罪企业的预期结果最好, 其给涉罪企业激励程度也最大。 在这种话语情形下, 企业更倾向于选择专项性的合规方式。 第二类是激励程度一般的话语,比如 “如果整改效果较好, 可能作出从轻减轻处罚的量刑建议”。 在这种情况下检察机关展示了较为确定且结果一般的处理话语, 但 “从轻减轻处罚”话语的激励效果明显低于 “相对不起诉” 话语。 此种话语预期结果一般, 其给涉罪企业激励程度也一般。 在这种话语情况下, 企业更倾向于选择纠错性的合规整改方式。 第三类是激励程度较低的话语,比如 “将以合规整改情况作为量刑酌情考虑或者量刑优待的参考”。 在这种情况下检察机关展示了较为模糊且处理结果一般的处理话语; 此种话语下涉
罪企业的预期结果较差, 其给涉罪企业的激励也较低。 在这种话语情况下, 企业选择纠错性的合规整改方式的倾向性更强, 甚至可能 “破罐子破摔”,仅仅采取表象上或者形式上的合规整改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