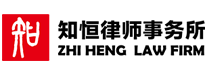正向与负向的刑事激励,分别指代“奖励”与“惩罚”两种对立的作用方式。对于已经建立合规管理体系或积极配合检察机关进行合规整改的涉案企业,应予以刑事上的优待;对于业已存在违法事实、消或拒绝配合检察机关进行合规整改的行为,应予以相应的刑事制裁。这种“赏当其劳,罚当其罪”的朴法理念植根于国家法治理念及社会公众法治意识,理应在企业合规的刑事激励制度安排中得以体现。
坚持正向与负向激励的相称性,不仅是对公平正义理念的坚守,还是域外合规实践的教训使然。早年,美国参议员们便提出过质疑:大型金融机构大而不倒(toobigtojail)的地位是否会削弱联邦政府起诉不法行为并实施适当惩罚的能力。当然,在制度安排上坚持正向与负向激励并重并不意味着削减正向激励,而是强调在建设正向激励机制的同时也应当构建相应的负向激励机制,两种激励机制的并重旨在避免企业合规的激励失衡,而非正向、负向激励的此消彼长。在制度的具体安排上,宜针对上文提及的失当情形作出以下修正:
一是加强对强制性措施的检察监督。虽然美国学界一直不乏对检察官利用暂缓起诉协议干预企业事务的批评,但在后安达信时代,签署暂缓起诉协议已成为企业应对刑事调查的首选。在我国,检察机关不仅行使着公诉裁量权,而且能够通过实施法律监督对侦查行为产生影响。对涉案企业而言,侦查阶段中的逮捕和查封、扣押、冻结等措施所产生的负向激励效果尤为明显,对此李玉华教授指出,我国的强制性措施在激励企业合规方面具有天然的本土优势。不过,对此类强制性措施的运用缺乏监督,导致此类措施恣意滥用的问题在实践中普遍存在。检察机关既是法律监督机关,也是企业合规改革试点工作中的主导机关,其复合属性为加强对强制性措施的监督提供了法律和事实上的正当性依据。具言之,在办理涉案企业犯罪的案件时,检察机关可依《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256条第1款之规定,在必要时提前介入,并对涉案企业的合规建设情况、合规意愿等因素进行考察,及时对强制性措施作出相应的调整,以弥补检察机关决定起诉或不起诉前正向激励的不足。
二是强化经济制裁的刑事威慑力。在谈及对涉案企业实施经济制裁时,有学者设想由检察机关促使涉案企业履行民事赔偿责任[28],也有学者构想以罚款金额作为确定企业认罪认罚的具体条件[29]。实践中,检察机关在办理涉案企业犯罪案件时会选择对涉案企业适用合规不起诉的同时,依据《刑法》第37条及《刑事诉讼法》第177条第3款之规定,对涉案企业处以行政处罚,避免发生一“放”了之的情形。在域外,对涉案企业实施经济制裁同样是实践中的惯常做法,例如,汇丰银行与美国司法部在2012年12月达成暂缓起诉协议,前者被没收12.56亿美元,除此以外,其还向货币监理署支付6.65亿美元的民事罚款、向美联储支付了1.65亿美元但正如我国实务人员所指出的,对于涉嫌犯罪的企业不起诉后,检察机关无权进行罚款,导致对企业的威慑力不足。在现有的制度框架内,行政处罚的严厉性受限是不争的事实,假若不能在刑事实体层面对涉案企业施加更严厉的经济制裁,那么检察机关就应当在刑事程序层面确保威慑效果得以实现。最高人民检察院2021年10月发布的《关于推进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第8条规定,对被不起诉人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经检察长批准,人民检察院应当向同级有关主管机关提出检察意见。该规定实际上也反映了检察机关对刑事威慑力过低的担忧,故而强调刑事司法与行政处罚的有效衔接,以确保企业的犯罪成本不低于犯罪收益。
刑事合规不起诉案例分析:2016年1月至2016年11月,Y公司、唐某以骗取税款为目的,在无真实运输业务的情况下,通过他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27份,虚开税款合计人民币18.6万余元,上述发票均由Y公司向税务机关申报抵扣税款。案发后,Y公司补缴全部税款。唐某主动向侦查机关投案,如实供述犯罪事实,自愿认罪认罚。
2019年10月,侦查机关以Y公司、唐某涉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向某市人民检察院移送审查起诉。审查起诉过程中发现,Y公司存在财务管控不规范、内部管理有漏洞、危废处理不合规等刑事风险点。检察机关针对上述风险点,向税务局、安全环保局、社会保障局等单位进一步了解核实相关情况。
2020年1月,检察机关建议Y公司在财务制度、危废处理、日常管理等方面加强刑事合规建设。Y公司邀请企业刑事合规专业律师担任公司独立合规审查专员,对公司进行合规评测,围绕企业运管、生产经营、财税申报、环保处置、应急管理等方面建立完善相关制度20余项。
2020年4月,检察机关召开不起诉案件公开审查听证会,邀请侦查机关代表、人民监督员、特约检察员等参加。与会人员一致认为,Y公司、唐某的行为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但虚开的税款数额不大、情节轻微、及时补缴了全部税款,且具有自首、认罪认罚等从轻、减轻情节,可以对Y公司、唐某作相对不起诉处理。次日,检察机关依法对Y公司、唐某宣告相对不起诉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