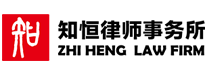基于优化营商环境、保护民营企业的初心,我国检察机关于2020年3月开启了“企业合规监管试点”的改革探索(下称“企业合规改革”),并确定了深圳市宝安区等6家检察机关作为试点单位,一定程度上标志着“企业合规改革”在中国正式拉开帷幕。2021年4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了《关于开展企业合规改革试点工作方案》,启动了第二期“企业合规改革”试点工作。第二期改革试点范围较第一期有所扩大,涉及北京、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湖北、湖南、广东等10个省(直辖市)。上述省级检察院可根据本地情况,自行确定1至2个设区的市级检察院及其所辖基层院作为试点单位。2021年6月3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财政部、生态环境部等9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建立涉案企业合规第三方监督评估机制的指导意见(试行)》(下文简称《指导意见》)明确规定,检察机关在办理涉企犯罪案件过程中,应当将第三方组织合规考察书面报告、涉案企业合规计划、定期书面报告等合规材料,作为依法作出批准或者不批准逮捕、起诉或者不起诉以及是否变更强制措施等决定,提出量刑建议或者检察建议、检察意见的重要参考。这意味着,企业合规改革的着眼点在于将企业合规激励机制引入批捕、公诉等制度之中,并使之成为对涉罪企业和负有责任的企业高管等自然人作出从宽处理的重要依据。从最高人民检察院2021年6月3日公布的4起企业合规典型案例来看,检察机关是通过将合规建设与酌定不起诉、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检察建议等方式相结合来激励涉罪民营企业进行合规整改的。而从合规引入公诉制度的路径来看,“合规不起诉”的实现路径大体上又具有检察建议和合规考察两种模式。有学者将合规考察模式概括为附条件不起诉模式。
虽然检察建议模式具有制发对象、时间灵活等优势,但是从有利于激励涉罪企业建立行之有效的合规计划方面来看,合规考察模式却有着检察建议模式所不具有的优势。这是因为,在合规考察模式下,检察机关通常会在审查起诉过程中,为那些被纳入合规考察的涉罪企业、相关责任人等设立一定的考察期,涉罪企业出具合规建设与接受考察承诺书,并在考察期内根据合规计划,完善企业治理结构,健全管理规章制度,规范生产经营模式,进而在考察期结束后综合其合规建设情况、犯罪情节等决定是否给予起诉。从试点实施以来的情况来看,几乎所有被纳入合规考察的涉罪企业和相关责任人,在经过6至12个月的合规考察之后,通常都获得了不起诉、轻缓量刑建议等宽大的刑事处理。
企业合规改革的大力推行,不仅会影响乃至改变检察机关在企业犯罪治理中扮演的角色,也会带来检察裁量权在涉企刑事案件中的扩张,尤其是在合规考察对象的确定上,检察机关必然拥有较大的裁量权。不同检察官之间的观念、办案习惯等方面的差异,难免发生“选择性”适用合规考察的问题,导致现实中类似企业犯罪处理不一致的情况。这无疑容易引发人们对检察机关主导的合规考察的正当性、公平性和平等性产生怀疑。好在,目前正在探索的“合规不起诉”本质上属于酌定不起诉的一种类型,检察机关由于普遍将自然人刑事责任追究与企业刑事责任的追究“捆绑”在一起。受现行《刑事诉讼法》的限制,试点检察机关通常也只是将相关责任人依法可能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涉企轻微刑事案件作为“合规不起诉”的适用对象,且酌定不起诉的适用程序长期以来掌握得比较严格,检察官不敢、不愿适用酌定不起诉制度,加上改革以来“合规不起诉”的案例还很少发生,人们对合规考察中检察裁量权滥用的担忧尚不是很大。
但是,随着企业合规改革的持续推进,未来立法上或将增设企业犯罪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合规考察的适用范围也将得到更加广泛的扩展,这必将赋予检察机关更大的自由裁量权。相应地,合规考察中检察裁量权被滥用的风险也会增加。改革决策者有必要未雨绸缪,认真对待涉罪企业合规考察制度的适用条件。笔者从涉罪企业合规考察制度建构的视角,以域外企业犯罪暂缓起诉协议和不起诉协议的适用条件为镜鉴,结合一些试点检察机关对合规考察制度的初步探索,从对象条件、证据条件、公益条件、配合条件、合规条件、补救条件等六个方面,对合规考察的适用条件进行评析和重塑,以为合规考察的适用确立更多的约束条件,从而对检察机关在合规考察对象确定上的裁量权进行规范。
摘自李奋飞《论企业合规考察的适用条件》
虽然检察建议模式具有制发对象、时间灵活等优势,但是从有利于激励涉罪企业建立行之有效的合规计划方面来看,合规考察模式却有着检察建议模式所不具有的优势。这是因为,在合规考察模式下,检察机关通常会在审查起诉过程中,为那些被纳入合规考察的涉罪企业、相关责任人等设立一定的考察期,涉罪企业出具合规建设与接受考察承诺书,并在考察期内根据合规计划,完善企业治理结构,健全管理规章制度,规范生产经营模式,进而在考察期结束后综合其合规建设情况、犯罪情节等决定是否给予起诉。从试点实施以来的情况来看,几乎所有被纳入合规考察的涉罪企业和相关责任人,在经过6至12个月的合规考察之后,通常都获得了不起诉、轻缓量刑建议等宽大的刑事处理。
企业合规改革的大力推行,不仅会影响乃至改变检察机关在企业犯罪治理中扮演的角色,也会带来检察裁量权在涉企刑事案件中的扩张,尤其是在合规考察对象的确定上,检察机关必然拥有较大的裁量权。不同检察官之间的观念、办案习惯等方面的差异,难免发生“选择性”适用合规考察的问题,导致现实中类似企业犯罪处理不一致的情况。这无疑容易引发人们对检察机关主导的合规考察的正当性、公平性和平等性产生怀疑。好在,目前正在探索的“合规不起诉”本质上属于酌定不起诉的一种类型,检察机关由于普遍将自然人刑事责任追究与企业刑事责任的追究“捆绑”在一起。受现行《刑事诉讼法》的限制,试点检察机关通常也只是将相关责任人依法可能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涉企轻微刑事案件作为“合规不起诉”的适用对象,且酌定不起诉的适用程序长期以来掌握得比较严格,检察官不敢、不愿适用酌定不起诉制度,加上改革以来“合规不起诉”的案例还很少发生,人们对合规考察中检察裁量权滥用的担忧尚不是很大。
但是,随着企业合规改革的持续推进,未来立法上或将增设企业犯罪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合规考察的适用范围也将得到更加广泛的扩展,这必将赋予检察机关更大的自由裁量权。相应地,合规考察中检察裁量权被滥用的风险也会增加。改革决策者有必要未雨绸缪,认真对待涉罪企业合规考察制度的适用条件。笔者从涉罪企业合规考察制度建构的视角,以域外企业犯罪暂缓起诉协议和不起诉协议的适用条件为镜鉴,结合一些试点检察机关对合规考察制度的初步探索,从对象条件、证据条件、公益条件、配合条件、合规条件、补救条件等六个方面,对合规考察的适用条件进行评析和重塑,以为合规考察的适用确立更多的约束条件,从而对检察机关在合规考察对象确定上的裁量权进行规范。
摘自李奋飞《论企业合规考察的适用条件》